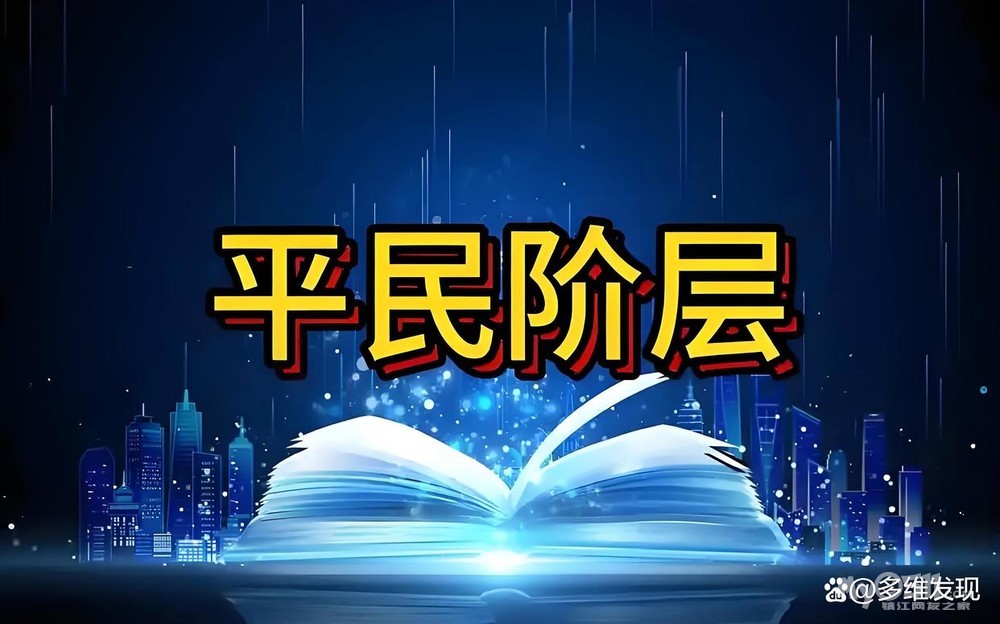穷人的社交,从根上就带着“资源贫瘠”的基因。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,你手里有别人需要的东西,别人才会给你想要的。可穷人能交换什么?工厂里的同事能帮你多抢个加班名额,小区里的邻居能借你一瓶酱油,菜市场的摊主能多给你几两葱——这些“帮助”撑死了让日子过得稍微体面点,却改变不了“穷”的本质。就像工地上的农民工兄弟,再铁的关系,也帮不了对方解决孩子上学的户口问题;小区里的全职妈妈们聊得再热络,也没法给对方介绍一份能兼顾家庭的好工作。他们的社交圈里,全是和自己一样“手里没牌”的人,交换来交换去,不过是把“穷”的焦虑互相传递,把“难”的处境彼此印证。
更残酷的是,穷人的社交往往是时间和金钱的负资产。为了“合群”,他们得凑钱随份子——工友结婚要去,邻居孩子满月要去,哪怕自己兜里只剩下个月的房租,也得硬着头皮掏出两百块买包烟当贺礼。为了“有人脉”,他们得陪酒、陪聊、陪熬夜——车间主任的酒局不敢不去,生怕被穿小鞋;老乡的聚会必须到场,怕被说“忘本”。可这些花费换来了什么?不过是酒桌上的一句“以后有事找我”,转身就被对方忘在脑后。有个在电子厂打工的年轻人算过账:每个月花在聚餐、随礼上的钱超过八百,占了工资的四分之一,可真当他想换个工资高点的岗位时,那些“称兄道弟”的人,要么说“我帮你问问”,要么干脆装没听见。他后来自嘲:“我这哪是攒人脉,是在给无效社交交保护费。”
富人的社交是“资源整合”,穷人的社交是“互相消耗”。富人的酒局上,递的名片能带来合作,聊的项目能落地赚钱,哪怕是一场高尔夫,都可能敲定几百万的生意——他们的社交像滚雪球,越滚资源越多。可穷人的社交呢?牌桌上输的钱,酒局上喝坏的身体,闲聊时浪费的时间,全是只出不进的消耗。有个开杂货铺的老板,每天晚上都和附近的店主聚在一块打牌,美其名曰“联络感情”,结果输了钱不说,还因为熬夜看店走神,收了好几次假钞。他老婆骂他:“你那些‘牌友’,能帮你挡假钞还是能帮你多卖瓶酱油?”话糙理不糙——当你的社交圈里全是和你一样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,所谓的“感情”,不过是一起浪费人生的借口。
社会早就用隐形的规则告诉我们:社交的价值,取决于你自身的重量。你自己是块石头,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;你自己是根稻草,再多人把你捆在一起,也漂不过河。工地上的工人再怎么和工头称兄道弟,工头该扣工资还是扣;小职员再怎么巴结领导,没业绩照样被边缘化。那些鼓吹“穷人要多社交”的鸡汤,要么是不懂底层的无奈,要么是故意装傻——他们没见过农民工为了请工头吃顿饭,省了三天午饭钱;没见过小商贩为了加入“老板群”,硬着头皮买了自己根本用不上的会员。这些社交不是跳板,是枷锁,把穷人牢牢锁在“假装很有路子”的幻觉里,忘了真正能救命的,是手里的技术、攒下的钱、读过的书。
当然,不是说穷人就该孤僻到底。父母生病时,邻居能搭把手送趟医院;下雨时,同事能顺便捎你一段——这种“雪中送炭”的情分,是日子里的光,该珍惜。但要是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社交上,指望靠“人脉”改变命运,那就是把幻觉当信仰。就像小区里收废品的老李,认识全小区的人,谁家有纸壳子都给他留着,可这改变不了他每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日子。他自己说得明白:“人家给我纸壳子,是因为我给的价公道,不是因为我‘会来事’。”
说到底,穷人最该警惕的,是把“社交”当成逃避现实的麻药。与其花时间琢磨“怎么和有钱人搭话”“怎么和领导搞好关系”,不如把精力放在能让自己变“重”的事上——学门手艺,考个证书,哪怕多攒点钱,都比那些虚无缥缈的“人脉”靠谱。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来很直白:你有价值,你的社交才有价值;你一无所有,别人的“兄弟”喊得再亲,也不会分你一杯羹。
烧烤摊的酒喝到最后,总会有人拍着胸脯说“等我发了财,忘不了兄弟们”。可天亮之后,该搬砖的还得搬砖,该摆摊的还得摆摊。那些在酒桌上许下的愿,就像啤酒泡沫,看着热闹,一戳就破。穷人的社交,大多时候就是这样——听起来有用,实际上,没什么毛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