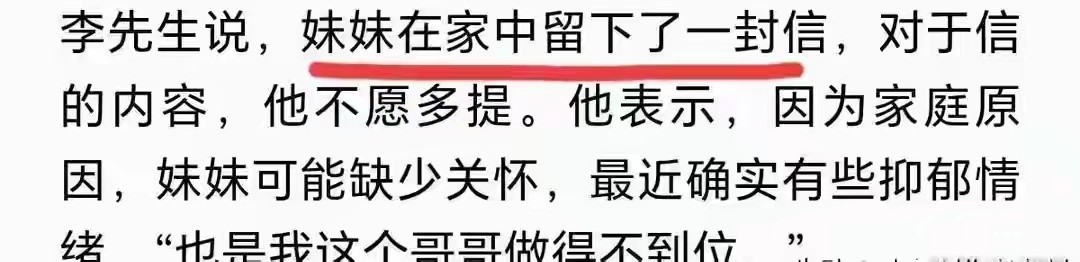她1月20号晚上九点三十八分出门,监控拍到她从北大学城地铁A口出来,手里攥着一本书,兜里只有几块钱。手机没拿——平时连充电线掉床底都要趴着找半天的人,那天把手机留在了出租屋桌上。
郑州那几天零下十二度,体感更冷,路上还积着雪。她穿得单薄,走的不是去医院的路,是往河那边去。没人拦她,也没人问一句“你今晚真上夜班?”她哥哥说,以为又是轮班,等凌晨四点人没回来,才开始打电话、翻监控、沿河喊。
她留了封信。哥哥没打开,只说“跟家里有关”,说了两次。没细讲,也没人再逼问。信纸折得整整齐齐,放在她枕头底下,像怕弄丢,又像怕被人看见。
贾鲁河那段岸,夜里黑,灯少,摄像头早被野草遮了一半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有人钓鱼掉下去过,有人坐那儿发呆不说话,也有好几个人再没上来。它不是什么“邪门河”,就是一条没被好好照看的河。
她工作在郑大一附院神经外科,值夜班,白天补觉,生活像上了发条。可发条松了,没人听见咔哒一声。邻居说她近来话少,但谁家妹妹不累?谁家哥哥不是一边打工一边顾家?没人想到,少说话、不发朋友圈、总说“没事”,可能是真的快撑不住了。
心理援助热线郑州有,110也接警快,可那天晚上,没人知道她正站在河边。报警后警方调监控、发协查,但没同步联系心理危机干预中心——这流程,现在看是空的。
她不是突然消失的。是慢慢变轻,轻到没人觉得她会沉下去。
那封信还在哥哥手里。
他一直没拆。